刚进科室,主任就把石良分成周老师带去了。 周老师是个瘦长的中年男子,眼圈黑,皮肤黑,整天一脸没精打采的样子。 作为“大师”,他对石良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啊,你必须训练能闭上眼睛睡觉的手臂。 如果能睡的话就能继续。 如果你抱着太多的心事睡不着,请早点离开急诊室。”
这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很忙,高峰期时,急诊医生的日均接诊量几乎都是从“百”算起。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更是要打一场场硬仗,来处理爆竹炸伤、打架伤、鸡骨鱼刺卡喉咙等各种意外问题的病人能挤满整个楼道。有一年除夕夜,光石良一个人就接诊了173位病人,他感觉自己说话像开了2倍速,好容易熬到交接班,等他整理完病历,才发现距离前一天接班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实际工作时间与排班工作时间不符,这在医院太常见了。
那会儿石良20多岁,精力充沛,还没体验过什么叫“力不从心”。他把废寝忘食地工作当成了骄傲,自己感动着自己。每天他在医院跑来跑去,平均每3个月就能穿破一双运动鞋。忙起来时,48小时不睡觉也是有过的。下班后,他还会去打球、健身。虽然周医生一个劲儿地提醒他要“注意休息”,但他有着自己的打算——他觉得自己天生身体素质好、领悟力强,只要趁年轻好好学习技术,积累经验,总有一天,他能在行业内发光发热,出人头地。
这年的冬天,石良跟着师父值“大夜班”,120从县医院拉来了一个女病人。患者41岁,脑梗、脑出血、肾衰严重,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的状态,县医院给出的诊断是:混合型脑卒中。
经过一番紧急检查,他们发现这名女患者还有甲状腺、电解质紊乱等问题,师父问石良有什么想法?从实习开始,脑卒中的患者石良见得多了,伴随各种突发性、慢性病发作的也见过,可程度如此严重的病人却很少见。石良答:“她不像单纯的混合型脑卒中,看她的片子,可不像是会重度昏迷的。”
师父点点头,就去和家属沟通了。患者的丈夫说不清前因后果,只记得老婆感冒了,使不上劲儿,于是就在村诊所打了一段时间的“能量针”,没想到打了几天后人就突然昏迷了。听他讲到这儿,师父突然想起了一张化验单,立即反应过来:“患者有糖尿病,怎么能随便打‘能量’?这相当于一直在给她补糖分,她怎么可能不昏迷?”
患者的丈夫很吃惊,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妻子还有糖尿病,石良顿时明白过来,这名女患者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混合性脑卒中。她昏迷后,家人把她送往县医院,医生拍了片子后就按脑卒中来治,但忽略了她的糖尿病,最终才出现了脏器衰竭等严重症状。
接下来,石良和师父对症下药,先纠正这名女患者酸碱中毒的问题,等昏迷程度减轻后就把她转去了神经内科。两周后,这名女患者转危为安要出院了,石良心里有种难以抑制的成就感:“嘿!又从死神手里抢回来一个人,我们治了个疑难杂症。”
可周医生却没多高兴,他说这不算疑难杂症,考验的只是临床医生的经验,很多小地方的医生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一例这种病例,所以才光治表不究根:“我都害怕万一我老了没行为能力的时候遇不上个有经验的大夫,那还不得提前结束人生啊?”
师父的担心,石良也有。他愈发觉着当医生,技术是排在第一位的,为此自己付出再多努力都值得。
在急诊科待了一段时间,石良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发现身边的同事交际面很广,他们既熟识片区内的警察,也认识不少地痞流氓、瘾君子、酒蒙子、催债人、借债人……
一天,石良和师父正说着话,就看见门口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是片区里的黄警官。周医生悄悄给石良使了个眼色,二人走出诊室,发现走廊的长椅上还躺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双眼紧闭,胳膊上的针眼清晰可见。
周医生的语气顿时不好了:“又是他啊,今天干什么了?是打针晕了还是挨打了?”
黄警官说:“估计又没钱了,跑马路上碰瓷儿去了,真行,又出了个新花样儿。”
长椅上的人名叫老乔,是个多次“进宫”的瘾君子,也是片区内出了名的大麻烦。以前他常和人打架斗殴,目的就是要输,只要受了伤他就能讹点儿钱当毒资。这次他更不要命了,竟然敢在马路上碰瓷儿,车主发现他不对劲,在几米开外就倒车了,结果他追上去扑在车上。因为没装行车记录仪,车主一开始打算认倒霉,给一两百元息事宁人。谁知老乔贪心,开口就要五百,还说,如果去医院检查最少得花千八百的,不如直接把钱给他。最后俩人没谈拢,老乔干脆躺在地上怎么喊都不睁眼,司机无奈,报了警。
石良跟着师父仔细检查了老乔的伤情,发现他除了因长期吸毒导致的心肾功能不全、高血压、肢体浮肿等慢性病外,没任何大碍。但无论怎么刺激他,他都不言语、不动弹,就是装死。周医生耐着性子又喊了老乔几声,见他还是一动不动,于是就转身对石良说:“推‘速尿’。”
“速尿”就是呋塞米,是一种能治疗水肿性疾病的药,它不仅对老乔的慢性病有好处,还有着特别强的利尿功效。除非意志力非人的强大,不然谁也抵不过“速尿”的威力,真晕和耍赖,用它一试就能试出来。术业有专攻,这也算是医生的损招了。
药水注射进去,不一会儿,老乔的脸上就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接着他脸上的肌肉越来越扭曲,虚汗直冒。大家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突然,老乔猛地跳起来,朝厕所冲去。黄警官大笑:“再没脸没皮,也怕这人有三急啊。”
石良有些意外,他本以为老乔会摆烂直接尿在裤子里,没想到他会去找厕所,还有为人的自尊心。周医生可能也发现了这一点,等老乔回来以后,由衷地劝道:“你也不小了,别碰瓷儿没落着好还把慢性病给勾出来,直接心力衰竭人没了,值得吗?”
老乔被黄警官带走,车主终于松了口气,他感叹:“我就说嘛,还能没地方说理了,社会还能由着坏人糟蹋了?本来我也想认栽拉倒,现在我不这么想了。钱可以花,理不能不讲,花钱买心安可以,买恶心不行!”
车主的话让石良感到一丝振奋,也生出了一种正义感,可等静下来,他又觉着挺无奈——也许过不了多久,他还会和老乔见面。
在急诊科工作的第四年,一个晚班,石良突然感到胸闷。他摘了口罩大喘气,却发现氧气走到一半就沉不下去了。师父看出他不对劲儿,赶紧把他的病人接手,让他去休息。
缓了一会儿,石良感觉好多了,他给自己下了判断:心脏早搏。以前他经常看到同事自己给自己看心电图,不用问,一定是心脏早搏了。对于他们这些生活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大夜的医护来说,心脏早搏很常见,一些年纪大的同事甚至还会出现胃肠功能紊乱、肾小球肾炎等问题。
第二天上午交接班结束后,师父把石良按在检查床上,非要给他查心电图不可——在大型三甲医院,每年都有医生因过劳猝死,这是很难回避的现实,但谁也不想看到悲剧发生在自己身边。
见石良无奈地笑,师父恨铁不成钢地问:“下了班还打球吗?”
“不了。”石良乖乖回答,“回去躺着。”
师父训石良,他不敢顶嘴,还要死皮赖脸地哄师父,因为他知道师父这会儿无论说什么难听的话都是为了自己好。同行因处境相同惺惺相惜,但作为医护想获取病患的理解和支持,就没那么容易了。
比如每年的秋冬季,是流感的高发期,医生护士天天待在医院难免中招,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病人们在留观室里挂吊瓶,医护在休息室里挂吊瓶。石良无数次看到同事听到紧急呼叫铃声就立即给自己拔了针头,然后匆匆赶往诊室。这种事,没有医护会拿出来说,病人、家属也不知道。
可在一些人的眼里,医护都是三头六臂的钢铁之躯,他们不会生病,更不应该有情绪。
一个冬夜,一条高速上出了重大交通事故,十几辆救护车紧急把伤者送来这家离得最近的三甲医院。一时间,急诊留观病房里挤满了人,外面的走廊也被临时病床占满了,伤者的呼救声、叫喊声此起彼伏,乱成了一锅粥。
已经下班的医生们被紧急召回,值班医生一刻也不敢停歇,插管的、心肺复苏的、联络专科会诊的、送病人赶往手术室的,大家忙得脚踢后脑勺。当时,周医生已经低烧两天了,正在休息室里打针,也都跑出来接诊了。等处理完伤者,他的脸都白了,居然还坚持开完了第二天的早会才回到休息室重新把吊瓶给自己挂上。
可就是在这个忙乱的夜里,急诊室还发生了一场意外。石良当时正忙着,突然脚下一滑,发现地上全是水。他回头一看,一对男女正各提着两大桶水轮流往急诊室里泼。后来大家才知道,他们搞这一出是为了泄愤——他们的家属发烧了,向护士要过两次冰袋,但护士太忙没有及时送到,两人就来了脾气。他们先嚷嚷着要投诉,可大半夜行政楼的人都下班了,于是他们就去医院超市买了4个大号水桶,要给急诊室“降降温”。
有人大喊:“护好机器!”护士们纷纷行动,有的去阻止两人继续泼水,有的跑到机器跟前连扯带拽,试图把电源线从水里抢出来。可是有些机器不能离人太远,更不能断电,护士们只好脱了外套把机器包住。
大冬天的夜晚,车祸伤者还在不断地被推进来,急诊室挤得连门都关不上,暖气一点儿用都没有。这帮护士姑娘脱了棉外套,脚踩在冰水里配合医生的救治,说心里一点都不委屈那肯定是假的。
后来,警察把闹事的男女带走,问他们有买水桶接水泼水的时间,自己去外面的药房买个冰袋不行吗?俩人理直气壮地说他们住院是花了钱的:“护士取个冰袋才多少时间,怎么就不给拿?”
经历了这件事,石良明显感觉自己有点累了,他开始反思:难道只是因为我们有医护的身份,就必须抛弃自我、做一个任打任骂的机器吗?
他终于意识到,无论干什么职业,人都应该多心疼心疼自己。
在一次夜班之后,不知是因为劳累还是没注意脚下,周医生当众滚下了楼梯,把一条腿骨摔成了三截。骨科主任调侃他:“小周,你才几岁啊?骨质就疏松了?”
周医生自嘲地笑笑,说自己摔倒是因为精神不济:“我已经很久没睡过整觉了。”
石良这才知道师父严重失眠,他的脸黑并不是天生的。周医生说,自己年轻时也睡得好,第一次焦虑得睡不着,是因为几年前的一场医闹纠纷。
当时,一个坠楼的男人在送来急诊时就不行了,他的半截身体已经撕裂,像个漏斗碗,就算大量输血也救不回来。周医生对他进行了救治,男人还是很快去世,家属也接受了现实,走完了所有流程。可一周之后,死者的妻子带着一群职业医闹来到医院,说是医生误诊导致了男人死亡,“我们要讨个说法!”
医院查阅了所有的病案后认为周医生的诊断处理没有过错,可死者妻子不依不饶,她和那群人天天坐在医院门口展示“大字报”,要求医院严惩周医生并给予赔偿。这事儿造成的影响很坏,急诊科主任为了保护周医生,就给他放了半个月假,让他回避一下。
“自那之后,我就落下毛病了。”周医生说,“这件事整整持续了一个月,那段日子我吃不下、睡不着,想过一切悲惨的结局,都做好了脱白大褂,甚至自掏腰包花钱买清净的心理准备——你试想一下,天天有人在医院堵你、臭你的名声,心得多大才能放下?反正我放不下。我生气又委屈,每天神经兮兮地钻牛角尖,再之后我觉着我变了,每件事都要想得很周密才会去做,睡前还要复盘在医院发生的每一件事,心里的事越来越多,我开始失眠了。”
后来,那群人见什么好处也捞不到,就自动消失了,可这事对周医生造成的伤害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他记住了那几个职业医闹的脸,之后他又在医院见过他们几次,他们每次拥护的家属都不一样,受害的医生也不一样。
石良也为师父感到后怕——如果当时他写病历稍有一丝不慎,一定会落人口实,陷入无尽的是非中去。周医生也说,这多亏了主任平时要求严格:“主任在病历上对你们几个‘一线’严格,是为了你们好,别嫌他骂你们。医生要保护病人,更要保护好自己,这世上好人多,坏人也不少。”
跟石良深聊过之后,师父就回老家休养了,大半年之后他的腿才彻底恢复。回到科室,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提离职,这让同事们非常吃惊。
那天,石良和师父一起出去喝酒,师父说自己受伤后天天躺在家里,医院的纷纷扰扰与他无关,他竟睡了几个月的好觉:“由奢入俭难,我当不了坏情绪的垃圾桶了。”
想明白之后,他火速去老家县医院应聘,那边一听他的工作资历和背景,恨不得他立刻入职。石良问师父:“你忘了那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事儿了?县上人少、病例少,技术不进步就是退步,你甘心?”
师父又拍了拍石良,说:“我40岁了,承认失败没什么的。我没有强大的精神,也没有强壮的身体,回去虽然收入少很多,但你知道吗——我观察过小县城医院的晚上,没人。”
师父边摆手边笑,脸上是少见的轻松。
周医生走后,石良成了没有“靠山”的一线医生,他感觉自己心里空落落的。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像师父,开始无比珍惜下班后的休息时间,但长期白夜颠倒造成的恶果还是显现了。
参加工作的第五年,石良开始频繁地发烧,尤其是在下夜班之后,有时他正在补觉、吃饭,身体就开始突然发热直至38.5度。这样一烧一下午或者一晚上,只要睡一觉,第二天就能好。石良心里明白,这是免疫力在下降,好得快只因自己还不老。
妻子心疼石良,不断地劝他别干了:“身体比事业更重要。”但石良还是放不下、舍不得、不甘心。在急诊科,他所学的专业技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锤炼,这份工作也让他得到了金钱、社会地位和价值感。他还不老,不想浪费自己。
夫妻二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一个病人的出现,点醒了石良。
那是一个超级忙碌的“大夜班”,抢救室、留观室连个站的地方都没了,走廊里躺满了120送来的病人,一团嘈杂。这时,一个50多岁的大叔独自来到急诊,石良闻到他一身酒味儿,以为又是个喝多了来打针的“酒蒙子”。
大叔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说自己吃了“麻辣螺蛳”这道菜之后就感觉想吐、头疼。此前,石良在这座北方内陆城市只见过大排档里卖的田螺和花螺,没见过其他品种,于是就问大叔是不是吃了腐败的螺肉。大叔一个劲儿地摆手,示意螺蛳是自己煮的,没坏,还说这个螺蛳的味道特别鲜,他老家的人都吃,“只要处理好就不会有事,这个螺我处理了”。
石良觉得大叔是微中毒,于是就让他打吊瓶,喝牛奶催吐。没想到半小时之后,大叔的呼吸停了。副主任闻讯赶来,冷静地听石良细述完病情,生长于南方的他立刻判断出了那个螺蛳的品种,接着他们迅速给大叔上了呼吸机和对症药品,呼吸终于恢复了。
“毒螺肉”事件让石良心有余悸,他想这位大叔应该也知道怕了吧。谁知没过多久,大叔又因食用螺蛳中毒来到急诊,他说:“我回去想了一下,上次中毒肯定是因为没把螺肉处理干净,这次我好好处理了,还把螺肉多煮了一下,没想到还是不行。”
因为贪吃,大叔又遭了一轮罪,石良突然意识到,医生只能治病,但治不了病人的“心瘾”。有些犟种病人不听医嘱,总因同样的问题来医院,比如糖尿病,医生不让吃糖,病人非吃不可;病人肺不好,医生让戒烟,可他们还是要抽很多……这些人控制不了自己欲望,却又把救治的希望全寄托在医生的身上。
大叔出院时,石良对他说:“不出意外,你应该还会来。你放心,你这情况我们已经全科学习过了,只是下次你挑个别人当班的时间来,别折腾我一个人了行不?”
大叔不好意思地笑笑,说他会尽量克制的。
回到家,石良把这事讲给妻子听,她立刻说:“你和他不是一样的犟种吗?明知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健康了,却还是欲罢不能。”
石良心里一颤,没有反驳,当晚他再次没有睡好觉。
一个休息日的午后,妻子发现石良的背上冒出了一个肿块,他站直了还不明显,但当他弯腰穿鞋时,他的脊柱右侧就像塞进了一个馒头。妻子难以置信地说:“怎么这么大呢?啥时候长的?”
石良赶紧去医院做了个超声检查,结果显示是脊柱肿瘤,医生看了也感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脊柱瘤?”石良的妻子当场就不行了,她瞪着红彤彤的眼睛盯着那张报告,一直喘粗气——他们的孩子才1岁,石良要是出了什么事,她怎么办呢?
石良先镇定下来,他知道脊柱上直接长肿瘤的情况太少见了,脊柱瘤一般都是转移瘤,而且这个瘤目前没有产生任何痛症,自己的其他器官也没什么不适。他拉起妻子冲上车,打算再换个医院检查。他们又先后去了两家大医院,全套检查做下来,终于松了口气——虽然这个肿瘤紧靠脊柱,但它只是一个巨大的肌纤维瘤,良性,增生性质,切除即可。
得到最终结论,妻子抱着石良哭出声来:“叫你别干了你就不听!人除了命,哪有什么舍不得的?别干了,一个夜班都不要上了!”
石良没有说话,此时的他已经在急诊科待了7年,这次真的要当逃兵了吗?
石良不想让同事知道自己病了,术前他还是照常上班。又是一个“大夜班”,120送来一个危重病人,医生们开始紧急抢救,石良负责做心肺复苏。一段时间后,石良的按压力度逐渐变弱,一个来急诊科轮转的年轻医生说:“换我来!”
就在他俩刚换了位置交接时,一个男人突然冲进抢救室,举起拳头重重地敲在了那位年轻医生的头上。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年轻医生毫无防备,捂着头倒在了地上,一旁的石良惊呆了——如果再早半分钟,被攻击倒下的人就是自己。
随后,保安、护士和急症病人家属一拥而上把袭击者拉出了抢救室。他袭击医生的原因不得而知,据说是“无差别攻击”,也就是说谁离抢救室的大门最近,谁就倒霉。年轻医生被打成了轻微脑震荡,其他医生没时间愤怒,还在继续给那位危重病人做按压。
那一瞬间,石良所有的迟疑、犹豫都化为乌有。
一周后,石良去了另一所三甲医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因为打的是局麻,主刀医生边做手术还边跟石良聊天。他问石良是干什么的,石良谎称自己是企业职员,医生又问:“你们加班是不是很多?你这不行啊,作息不规律可毁身体呢。”
“你呢?”石良反问。
主刀医生愣了一下,说:“嗐,不提也罢!医不自治,都是说人家嘴长在前面,到自己嘴就长脑袋后面了。”
后来,石良跟妻子聊起这位医生,还忍不住吐槽他手慢、不灵活:“要是我,手起刀落,‘唰唰唰’就切了。”
妻子说:“至少人家身体好,能扛住造,这就赢了你。”
伤口恢复后,石良的后背多了一道长长的疤痕。2019年年中,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万般不舍地脱下了白大褂。离职后,他去见了师父,俩人又喝了一场酒。
石良说:“幸亏是良性的,不然这会儿你怕是都见不到我了。曾经我想要年少有为,结果人到中年发现,理想没PK过身体。”
周医生已经喝到微醺,他笑了起来:“理想也是要讲条件的,医院离了你不是照样挺好?向前看吧。你知道我现在每天几点睡觉?11点前。”
石良离开了医院,却没有离开医疗行业,他选择了医生转行最容易上手的医疗器械销售工作。他掰着指头算新工作的好处:能双休,有年假,出差可以心无旁骛,逢年过节可以跟家人团聚……那些好处居然用一双手都数不过来。
可是,真正进入新行业,石良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外面的世界并没有他想象中的美好,毕竟哪一行的钱都不好挣。想要做好医疗器械销售,说白了得靠人脉,好在石良在“大三甲”工作了7年,认识不少同行。只是,过去石良做医生时算是甲方,多少人求着他办事,现在他成了乙方,为了谈成一笔生意,求人成了常态,也很容易被人“拿捏”。
他走后,前单位换届,新的领导班子大刀阔斧地清算“陈年旧账”,医院里人人自危。一天,石良突然收到一位前领导发来的消息,求石良帮自己“扛个雷”。他说,反正石良已经离职,跟医院没什么关系了,“你帮我把事儿顶一下,罚款我自己缴。我要是背个处分,至少十年八年别想朝上走,但你只要缴了罚款就两清了,院里的事儿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
石良不能拒绝。在商言商,他现在的生意靠的都是过去积攒的人脉,原单位的人他一个都不能得罪。于是,他羞耻又无奈地帮前领导背了这个黑锅。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看着曾经的同事有的开拔支援湖北,有的在重症病房里冲锋陷阵,石良感觉自己当了逃兵,这让他耿耿于怀。他说:“早知道会出这事儿,我就再多扛两年,我是真不愿意承认自己没有当医生的天赋。”
他总想为抗疫做点什么,哪怕跑跑腿儿当个支援也好。在疫情刚开始那会儿,医院的防疫物资十分紧缺,石良四处联系渠道运送口罩、酒精;疫情高峰期时,一些医护人员被隔离在医院里,他又联系商家,给大家配送隔离晚餐……
至于年轻时的理想,石良说:“人嘛,好歹有点精神追求,值不值的我早都不想了,反正我经历过了,然后做了当下最优的选择,争不过命就不争,老老实实按自己条件活着,这叫‘定制人生’。”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魁葵)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


 相关阅读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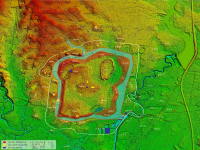




 近期热点
近期热点
 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