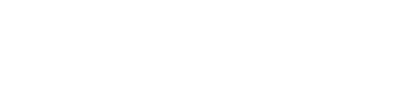


获知同伴的噩耗,丁硕徵觉得疲倦而厚重:迄今为止,她们确保了队友零感柒,却不曾抗住她们倒在一线。
4月12日,他的同伴,54岁的曹进胜在执行任务时忽然倒下,救治后不管死亡。
丁硕徵是厚天应急救援总队的副总队长,他所处的机构是上海唯一的民企地市级社会性应急救援团队,担负了一些紧急每日任务。从3月11日起,丁硕徵就带上队友在地铁口、商场、企业、住宅小区等做消杀。
消杀要求非常大,丁硕徵说,3月28日,浦东封控时她们的工作量早已贴近高峰,一直维持到现在,与日俱增。热线电话每日要接四五十个拨打电话,有小区业主说想团“消杀”,但就算是有呈阳性患者的住宅小区,排长队也需要等上两三天。
丁硕徵有时会感到挫败,这个小区明明刚消杀过,为什么又出现病例了。看不见的病毒,要跟它抢时间。
消杀的药箱灌满消毒水,有三四十斤,相当于部队里单兵装备的重量。消杀队员要背着它,弯腰作鞠躬状,作业全程。防护服和N95口罩不透气,整个人很快就会湿透,丁硕徵说,消杀结束,他们脱下防护服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
【以下为丁硕徵的自述】
在老小区做消杀
3月11号,我们总队要求上海地区的各支队伍进入应急备勤状态,做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准备。那时候开始,各个救援队伍的力量基本都扑在疫情防控上面,包括做消杀、应急保障、应急处置、应急转运等、陆上应急保障、水上应急保障等。
像我的话,从3月11号到现在,一天都没有休息过。基本上早上七八点钟到任务地点集合,在地铁站、超市、公司、小区等做消杀,一直持续到晚上,中间还会接到一些群众的求助电话,调度各个队伍的工作任务,一刻不停地收发消息。
3月24号,我所在的小区有阳性病例,小区封控管理,我就没有回家。直到4月3号,有几天时间,我都睡在自己车里,因为车上不能躺平,基本上睡两三个小时就醒了。

后来,我在同事家借住了几天,有了洗澡的条件,但住在别人家里肯定不方便,晚上睡在沙发上面,也休息不好。前几天,上海进一步规范了通行证,拿着通行证可以回社区,4月12号,我就赶紧回家了。
目前,厚天应急救援队在上海的人员大概有三百人,由行政人员接听求助电话,把情况记录下来。我们总队再根据现有的力量,进行任务的协调和指派。
几天前,接听热线的同事告诉我,每天大概接到40-50个电话,他们会筛选出真正需要帮助的对象,派就近的队伍去做消杀。像一些地方的需求如果不是那么紧急,可能会往后排,等待两三天左右。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3月27号,黄浦区某街道发来的一个求援函。那是一个老小区,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小区里出现了几十个病例,可能由于“120”调配不过来,部分阳性患者还在小区没有被接走。
当日中午,我领队去那一个住宅小区做的消杀。居民见到大家技术专业消杀团队来啦之后,如同看到了救兵一样,十分相互配合,十分激情。
住宅小区一共有五排楼,一排有三四栋楼。老小区租房较为划算,有许多是同租的。呈阳性病人比较多,大家专业技术人员内心也焦虑不安。手套平常只戴了一层,那时候戴了双层,鞋套、手套戴好后,大家把衣袖、牛仔裤子全部包进来,还需要拿透明胶带再缠起來。
消杀的情况下,我发现这一住宅小区的快递公司、外卖送餐太多了。由于老人尤其怕家中沒有菜,一直找他人代买烟、代买水果,此外,沒有被感染的居民经常下楼买一些不必要的物件,产生了安全风险。
住宅小区里几幢有呈阳性患者的楼被封号了,楼栋下边都拉了警界线,有衣着防护衣的青年志愿者驻守,但别的楼栋的居民还能够下楼在社区里主题活动。乃至被封号了的楼栋,也有居民打开窗户讲话,一说话飞沫传染就出来。
但除开进行消杀每日任务,大家也帮不了哪些忙。由于她们沒有对应的消杀机器设备。现阶段,全部的消杀工作全是由第三方在做——在上海,消杀工作是这轮新冠疫情里才起來的,在这之前,从业人数也很少。
现在能承担消杀任务的,第一是各个应急救援队;第二,很多保洁公司有消毒液、喷壶等消杀设备。
“持续到现在,消杀需求有增无减”
3月28号浦东封控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量已经接近高峰了,一直持续到现在,消杀需求有增无减。
很多是业主自发打来的,像团购蔬菜、鱼肉一样,他们想团个消杀。小区业主说,居委会只有几个人,管理几千个人的社区,是管不过来的,他们要“自救”。
打电话过来的社区有阳性病例的,紧要程度是一样的,按照先后顺序,通常要三天才能排上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进一步规范了消杀条件,要求阳性病例拉走了才能去消杀。如果阳性病例没拉走就消杀,等病例拉走了,还要再去一次。
消杀过程中,会有居民求助,希望给自己家门口单独消杀一下,或给他的车子消杀一下,也有人希望消杀队帮忙在外面带点东西进来。能够帮到他们的,都会尽量去帮。
最近上海疫情严重,大家基本上都戴着口罩。(但是)在小区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不规范的动作,比如说排队做核酸检测,有的人像玩一样,一边排队一边接电话,话讲多了,他就把口罩拿下来了。
我们现在的工作更偏重社区的消杀,特别是一些老年社区。一些条件好的社区,有渠道和资源自己解决困难。
像房龄三四十年的老旧小区,不少老人买不了菜,也不会用手机团购,微信支付。有些老人的口罩都戴破了,起球了,他们也舍不得更换。
3月底做消杀的时候,我遇到一位老人,他的牙掉了,说的本地话也听不懂,他耳朵又聋,交流很困难。我听懂了零星几个词,(大意)就是他家里没有吃的了,他也没办法跟别人交流。我能做的就是耐心听他讲话,把我听懂的反馈给居委会,看到他口罩都没有了,我给他一包口罩。
据我观察,小区居民永远在“缺东西”的路上。比如说居家隔离一两天,喝点稀饭,吃点菜,忍一忍没关系。但居家隔离一个月,单靠发放的物资很难解决全部的生活需求,包括卫生纸、尿不湿、奶粉、牛羊肉这些需求都出来了。还有一些非必要的需求也需要释放,想喝奶茶,点炸鸡,退而求其次,买点鸡米花和薯条,自己用空气炸锅搞一下。
“最大的困难是克服疲劳”
消杀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克服疲劳。
4月12日下午2时,上海厚天卫生防疫救援队队员曹进胜在执行任务时突然倒地不起,叫了“120”也没救过来。他当时在执行消杀和防疫物资搬运任务。
我当时没在现场。根据公司的资料,他是1968年出生的,福建南平政和县人。2006年以前,他都在老家做运输服务,2007年来到上海,开过超市,做过饮用水配送员。
2019年他加入的救援队,在队友印象里,他是个简简单单、本本分分的人,性格比较内向,家里有两个儿子已经成年了。平时妻子在家看孙子,他在外面抗疫,家人也都比较支持他。
14号早上,我接到他们卫生防疫救援队队长的电话,问我队里面怎么处理,我们经过一天的商议,决定通过公众号发布曹进胜同志的讣告。由于疫情,追悼会也一切从简,已经火化了。
目前为止,我们保障了所有的队员零感染,但是没有防住队员倒在一线,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做消杀工作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迷雾枪非常重,加上背的药箱灌满消毒水,有三四十斤,相当于部队里面单兵装备的重量。此外,迷雾枪的体积很大,一些窄小的楼道,没有电梯,需要穿着防护服,背着迷雾枪爬到六楼。
消杀是不走回头路的,按照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顺序消杀。我们得先到小区最里面,从顶楼开始工作。作业人员消杀的时候,一直弯着腰,保持鞠躬的动作。防护服和N95口罩不透气,整个人很快就会湿透,口罩里都是哈的气。
每天一组队员可以完成两三个大型社区的消杀,或是四五个小型社区的消杀。长时间穿着防护服,加上体力劳动很容易出汗,皮肤会起红疹,疼痛瘙痒很难忍耐。
通常一个社区要干两个小时,不间断地大家轮流上,一支迷雾枪灌满药水能用15分钟,枪打完了,志愿者把新的药水也灌好了。相当于人不休息,枪休息。因为一辆车上不太可能带那么多桶,我们会带几桶原液,原液用多少调多少,现场调配药水。
每次消杀结束,我们脱下防护服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每个人饮用水消耗量都很大,一天要喝好几瓶矿泉水,都不上厕所,因为都被汗排出来了。
用酒精或免水洗手液洗手,一旦喷上酒精,就会有刺痛的感觉。迷雾枪实在太快了,上面的铁片一不小心就会划破手。我们去有阳性病例的小区消杀,通常戴两层胶皮手套,但还会有手指开口的情况,也存在感染的风险。
很多时候顾不上吃午饭,因为一直会有人在催你。比如说安排下午过去消杀, 街道、居委会或者业主可能12点多就打电话催了。上海封控管理以后,没有餐饮店开门,我们基本上没吃过热乎的饭。依靠队伍的物资补给,大家要么坐在马路牙子上吃自热饭、泡面,要么坐车里吃,但车里也只能坐得下几个人。
在很累的情况下持续地冲锋陷阵,我也有过心脏不舒服、头晕或者濒临猝死的感觉。我都记不清什么时候了,因为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感觉,但都扛下来了。
那些求助电话里的无奈
最近大家都有一点“疲掉了”的感觉。觉得已经干了一个月了,天天在干,但是感觉没有效果。这个小区我今天明明消杀过了,但是第二天又报阳性了。
病毒无法用肉眼看见,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这些都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挫败感。
如果有队员突然跟我说太累了,心脏不舒服。我都劝他赶紧休息一下,明天不要出来接任务了。现在,我们会有选择性地接消杀任务,还要顾及队员的休息。
消杀过程中,遇到暖心的居民,拿一些物资给我们吃,比如泡面,矿泉水,能够直接拆包装吃的食物,我们不要,他们就扔到我们车上。还有的小区,消杀结束后,物业人员、居委会的人员在车队离开的时候,排成两列夹道欢送我们。
但也有碰到一些居民的“冷脸”。我们在社区消杀(价格很低)几乎是免费去做的,但有些老百姓会觉得我们是政府请过来,有付费给我们。对我们指手画脚,让我们帮忙搬东西之类。
其实,每天都有一些求助电话是出于无奈打到我们这里的。比如说一些需要血透的、得哮喘的、癌症需要化疗的患者,没有地方就医,也会打到我们这里。
4月14号,我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他是一个癌症患者,需要化疗。他以前去瑞金医院,瑞金医院跟他讲停诊三个月,也没办法帮他联系转院。他打给一家医院说停诊了,再打给另一家医院也停诊了,他不知道应该找谁,就希望我们为他提供一些渠道帮助。
我只能通过私人关系,找一些合作过的医院单位认识的医务人员帮他问一下。但他们现在都很忙,焦头烂额的,肯定要优先干自己的工作。我目前还没帮他找到解决办法,还在等消息的过程中。
此外,我还接到过小区业主想自己掏钱给居委会、志愿者买防护服的求助。应急救援队有一定渠道能够买到防护用品,队里的仓库也有应急物资储备。但基本是不对外卖给小区的。只能是去他们小区消杀的时候,车上有多余的,送给他们几件。
还有一个小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都是阳性,被封控在家里。委托了一个居民跟我们对接小区消杀工作,现在他们小区居委会负责的对接工作,都是他一个在搞。
队伍在消杀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站在旁边,观察这些居委的人到底有多忙。有的人专门负责接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一刻不停。还有人在小区里维持秩序,用喇叭喊,让居民待在家里,现在小区要消杀。但还是会有个别居民在小区里溜达,居委只能一个一个地去劝返。有时候觉得,就算我自己去做这个事情,也是没有办法。
“像一滴水滴进入大海”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去年大学毕业后加入的厚天应急救援队。
我们有一套类似军衔的衔级体系,来管理队伍。因为救援这个事情跟打仗是一样的,有黄金72个小时,黄金24小时,争分夺秒。在救援现场,必须要服从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本次上海新冠疫情的消杀工作,和上年我们在河南洪水灾害的援救当场不一样,最首要的是铺充足的人力,不断地、反复地做。许多住户问我讲,是否消杀之后就可以了?我讲并不是的,只需工作人员是流动性的,一直必须消杀。
大家有一个专业承担消杀的职能部门是卫生防疫救援队,也是放弃朋友曹进胜所属的团队。这一精英团队日经常出现四五十人,但远远地达到不了目前的要求。
如今,大家每天早上在每日任务地址结合,夜里每日任务完毕后,大伙儿将每日任务车子分散化开回家,尽量防止集中化被封号在了一个地区。第二天驾车回家的队员,再接好别的几个人出每日任务,由于通行卡是跟车走的,一辆车一张证。
拥有通行卡后,队员只需向社区居委会表述是市区的疫防工作人员,都能够出入住宅小区。可是有一些队员回家之后,很有可能得到了一些隔壁邻居的嘲讽。有一些隔壁邻居立即在群内说,你总出出进进的,危害我们的安全性,你要不就不必回家。大家都期待快一点解除限制,但听了这句话是多少有点儿心寒,大家在外面也是在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4月12号,在我回家以前,家中早已一个月没有人住了。我爸妈全是政府机构工作员,在抗疫战地早已一两个月没回家了。
大家把救援队全部的能量、資源都铺在消杀工作上,但觉得像一滴水滴进海洋,能量很微不足道。消杀需要量仍在提高,只有说竭尽全力这一事儿。
队员们累了,互相之间也会开玩笑。调侃说:“你去吧,你穿防护服,背枪进去,我休息一下。”但一旦碰到有阳性的楼栋,大家都说:“算了,我来吧。”正常情况下,需要两三个人轮流上一栋楼消杀,总会有队员站出来,要求一个人负责有阳性的楼栋消杀,一支枪喷完了,再下来换一支枪上去。



